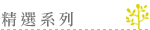主題精選


成長就是一場逃亡──電影《送信到哥本哈根》
作者:王怡
資料來源:期刊 - 2012春季號 - 2012-01-15出版
文章類別:信仰與靈命
文章主題:禱告/醫治|試煉/苦難|聖經人物|見證分享|其它|教育成長|見證分享|其它|見證分享|其它
關鍵字:大衛|苦難
一個孩子非同尋常的逃亡,隱喻著每一個人的生命成長。電影原著《我是大衛》中,作者將一場從東歐到北歐的地理意義上和政治意義上的逃亡,超越人類的世代,而描繪成一個關於永恆和生命意義上的成長寓言。
十二歲的男孩大衛,從二戰後的保加利亞勞改營逃亡,穿越了幾乎整個歐洲大陸,去尋找母親、自由、信仰和「一個有國王的國家」。影片開頭,大衛趁著停電半分鐘,那一場緊張而靜悄悄的越獄,也許是電影史上最美好的越獄鏡頭。一個孩子非同尋常的逃亡,隱喻著每一個人的生命成長。看這部電影,是因為讀到原著小說的中譯本《我是大衛》(宇宙光出版),也因為我將為人父,大衛的逃亡與成長,以及電影中這孩子的眼神,實在有一種我在影像和文字中許久沒有遇見的光芒。在瑞士,當大衛遇見的那位女畫家說:「有人打碎了這孩子的靈魂。」我的心痛,就像心痛自己未來的孩子,以及心痛自己。
一九六三年,丹麥女作家安娜‧洪在冷戰的鐵幕下創作出《我是大衛》,將一場從東歐到北歐的地理意義上和政治意義上的逃亡,超越人類的世代,而描繪成一個關於永恆和生命意義上的成長寓言。數十年來,這本書成為青少年成長小說的一部經典。二○○四年的電影改編也獲得成功,扮演大衛的那位童星演技驚人,在幾個電影節上得到新人獎。中譯本先在台灣出版,獲得了《中國時報》二○○五年的「最佳青少年圖書獎」。
大衛的父親是英國人,帶著全家去保加利亞幫助抵抗蘇俄的擴張。在勞改營中,一個典獄官愛上了大衛的母親,卻處死了她的丈夫,然後幫助她逃亡到了丹麥。
在離職的前一個晚上,這位典獄官再次安排了大衛的越獄,他沒有告訴大衛真相,只叫他帶一封信去哥本哈根。於是這個在陰暗的勞改營滿懷憂鬱、戒備、「不會笑」的孩子,孤身上路,開始了曠野中的流亡和成長。電影《受難記》的主角吉姆‧卡維佐,扮演了大衛在勞改營中的朋友和精神導師約翰‧尼斯。尼斯告訴大衛一定要逃出去,才能得著美和自由。他對大衛說,從前以色列有一個國王也叫大衛,寫過許多讚美詩。尼斯常為大衛背誦另一個大衛的詩,「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,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」。
大衛問:「他們為什麼要把我們關起來呢?」尼斯回答,「因為他們恨那些相信上帝的人。」大衛氣憤地說,讓他們去死吧。尼斯搖頭說,永遠不要這麼說,也不要這麼想。他幫助大衛學會仰望自己所相信和依靠的力量。在逃亡的路上,大衛發現自己實在一無所有,他對自己說,我也必須要有一個神,好向祂祈求。在勞改營中,大衛聽說過各種各樣的神,於是他想起尼斯為他背誦的聖經詩篇二十三篇,決定從此要向那一位「青草地和安歇之水的神」祈禱。小說中,大衛的那些禱告非常可愛。假若父母是無神論者,孩子們多半就會把父母當作神,想要什麼就向父母開口,而且一定要得到。最初的成長,就是當他終於發現父母不是神,不能滿足他的渴望,就開始轉向其他的「神」,或者接受世界的荒涼。但大衛學會了向他的「青草地和安歇之水的神」感恩,他祈禱說,我很慚愧,現在沒有什麼可以回報祢的。有一次,當他勇敢地衝入火宅,救出小姑娘瑪麗之前,大衛禱告說:這一次我不要祢幫,讓我自己來,給我一個回報祢的機會吧,我是大衛,阿們!
到了後來,大衛和他心愛的流浪狗遭遇到一次危難,終於明白了祈禱不是一種交換,原來真正的信心出於白白的恩典,而不是用回報去賺取一個願望。可惜好萊塢在一種「政治正確」的傲慢和顧慮下,在電影中竟用一個寓言式的偶像崇拜,替代了小說中的聖經詩篇二十三篇。電影裡一個麵包師給了大衛一個「伊莉莎白像」,說這是麵包的創始人,有什麼需要向她祈求,她就會保佑你。
這一討好世界的改編成了電影最大的敗筆。它將一個孩子的心靈世界簡化了,也羞辱了。小說裡大衛對信仰和自由的那些孩子般的思考,被好萊塢強行扔進了另一個勞改營。我彷彿又聽見大衛問尼斯,他們為什麼要篡改我的故事呢?尼斯回答,因為他們恨那些相信上帝的人。
我先看電影,後讀小說。電影裡的大衛令我心疼得想要收養,但小說中的大衛卻更令我對生命的成長滿懷敬畏。每個人都要經歷自己的曠野,亞伯拉罕、摩西、施洗約翰、使徒保羅,都在曠野的流亡和沉默中得到生命的澆灌。連基督也是如此,先獨自經過曠野,再以祂的話語返回人群。就如最初的創世,上帝在祂永恆的寧靜中,用祂的話語打破了祂自己的寧靜。當我低頭看一朵花,回首瞥見一個孩子的奔跑,或面向內心澎湃的憂傷,我會禁不住想,這一切就是上帝打破祂永恆寧靜的表現。
連孩子也不例外。專家們稱為「社會化」的過程,我稱之為孩子打破寧靜、走過他生命第一個曠野的旅程。就像大衛穿越整個歐洲,他像一個旁觀者,看見每個成年人都活在自己的完整世界裡。但對他來說,整個歐洲只是一個曠野,就像艾略特在《荒原》裡說,沙漠不只在南方,沙漠也在倫敦橋上。大衛走過鄉村、城市,在他遇見的每個人的生命縫隙裡鑽來鑽去。就像在森林裡鑽來鑽去一樣。一個孩子就算天天和父母在一起,他也是曠野裡的大衛。是誰的話語,讓他進入人群,終於凡事和我們一樣?一樣相信,或一樣不相信;一樣的罪,或一樣的赦免。一樣的月光,一樣的日頭,照在孩子們的身上。
大衛的逃亡之旅,儘管一切都缺乏,但有三樣東西卻是他最愛惜的必需品。這三樣恰好隱喻了他經過曠野的生命成長,一是肥皂,二是鏡子,三是羅盤。越獄之前,大衛向幫助他的看守開口要的唯一東西就是肥皂。大衛覺得,自由是和清潔有關的。當他在陽光下,用一小塊肥皂把「營區的味道和感覺」全都洗掉了之後,他開始覺得自己是大衛。「如果一直有肥皂,我就一直是自由的人」。肥皂成為生命的象徵,因為只有被潔淨的人才有自由,有自由才有活潑的生命。
在電影中是大衛從軍官室偷了這塊肥皂,軍官要槍斃小偷時,尼斯把那塊肥皂從他手中搶了過來,站出來替大衛死。卡維佐再一次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,這是一處最精采的改編,使肥皂的象徵意味更令人心動不已。
鏡子則是真理和智慧的象徵。在勞改營中,大衛一直不知道自己是誰,從哪裡來,要到丹麥去尋找什麼。他甚至連自己的長相也不知道,因為囚室的鏡子掛得太高了。越獄後他開始照鏡子,學會了笑。起初,他懷著對世界極大的畏懼進入這世界。但藉著一面鏡子,大衛慢慢擺脫了勞改營的捆綁,學會了接納、幫助和信任。鏡子促使他思考,當他吃橘子皮時,他說,「如果我連什麼好吃、什麼不好吃都不知道,怎能說我是一個自由的人呢?」大衛一開始,在別人面前假裝自己是馬戲團的,後來他發現自己是一個自由的人,因為他有能力思考。他說:「從此我不會再假裝自己是其他人了」。
而羅盤顯然是道路的隱喻。大衛的第一次禱告,就是當羅盤掉進大海之後。人若自以為知道方向,就不會舉目仰望。還有一個有趣的情節,大衛在勞改營聽人說在歐洲「有國王的國家都是自由的」。他逃亡時便不斷問別人,英國有沒有國王,丹麥有沒有國王。他說,我相信一個國王「不會覺得自己有權剝奪別人的性命和自由」。
這不是對一個君主立憲國的浪漫想像,而是生命意義上的一種國度觀。這裡的「國王」,就是大衛詩篇和哈姆雷特的王子身分所指向的那個「宇宙性的王」。
每個人的生命裡都有自己的國王,和一個靈魂深處的寶座。生命屬於一個靈魂的國度,如果戀愛是尋找白馬王子,成長就是尋找一個真正的國王。成長就是從一個國度向著另一個國度的逃亡,從勞改營的為奴之地,向著應許之地逃亡。直到最後在「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邊」得到安息,確定那至高的寶座上,到底是誰或什麼坐著為王。
經過了肥皂、鏡子和羅盤,大衛越過他的曠野,終於來到哥本哈根,敲響了母親的房門,有鼻子有眼地說出了這句話:「我是大衛」。
看過電影,讀完小說,我又有怎樣的確據,說我是誰?有人說,每個中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秦始皇。一個宇宙性的帝制是人永不可能廢除的,當人們推翻了一個紫禁城裡的帝王,每個人就在自己的心中登上了帝位。我們的身體就是我們的紫禁城。我們的孩子呢,要他像我們,還是像大衛?
(作者為成都秋雨之福教會的教導長老、家庭教會的傳道人;本文轉載自《天堂沉默半小時》p.10~p.15,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發行,蒙允轉載,特此致謝。)